扫码或长按识别,获取最新文昌本土故事、传统文化与地道美食资讯,与我们一起看见家乡的美好。

如果,你闭上眼睛回想文昌老家,听觉里最先浮现的声音是什么?
不是海浪拍打礁石的轰鸣,也不是老爸茶店里的喧嚣,而是老屋后院里,那一声声节奏分明的——“咯吱——咯吱——哗啦!”
那是压水井的声音。

在自来水管还没像血管一样爬满文昌各个村落之前,这口铁锈斑驳的压水井,就是一家人的心脏。它立在椰子树下,立在红土地上,不知疲倦地吞吐着清冽的地下水,流淌过我们贫瘠却又富足的童年。
01 一瓢“引水”,是生活的哲学
对于在文昌长大的孩子来说,压水井是童年的第一个“大玩具”。
那时候个子小,还够不着那个长长的铁把手。每次看大人压水,都觉得那是一种神圣的仪式。
压水井是有脾气的。它虽然守着地下暗河,但如果你两手空空地来,它便一点面子也不给,任凭你把铁杆压得震天响,壶嘴里吐出来的也只有几口干涩的空气。
这时候,阿婆总会像变戏法一样,从旁边备好的水桶里舀出一瓢水,从井头上方那个口里倒进去。这叫“引水”,文昌话里有时叫“吊水”。
那一瓢水倒进去,仿佛唤醒了沉睡的巨龙。手柄瞬间变得沉重,那是大地深处的吸力。紧接着,“咯吱”声变得敦实有力,只需三两下,一股清泉便如银龙般喷涌而出,撞击在水桶底,发出清脆的欢歌。
“先予后取,以小引大。” 这是压水井教给我们的第一个人生道理,比课本上来得更早,也更深刻。
02 那个没有冰箱的26℃夏天
现在的夏天,命是空调给的;而当年的夏天,快乐是井水给的。
文昌的日头毒,尤其是午后,地面烫得能煎蛋。但只要有一口压水井,暑气便退避三舍。
那时候没有冰箱,压水井就是天然的冷藏室。阿爸从地里摘回来的大西瓜,直接丢进刚打上来的井水里。井水温度恒定且冰凉,泡上半个钟头,切开来咬一口,那股沁人心脾的凉意,能从喉咙一直激灵到脚后跟。
那是文昌小仔最野的夏天。男孩子们光着膀子,围在井台边。一个负责压水,一个蹲在出水口下。
“快点!再快点!”
水流冲击在背脊上,比现在的花洒带劲多了。那种透心凉的畅快,伴着肥皂的清香和伙伴的嬉闹,是记忆里最奢侈的SPA。洗完澡,顺手在井边冲掉脚丫上的红泥,换上背心,坐在椰子树下乘凉,风都是甜的。
03 井台边,流淌着母亲的芳华
如果说压水井是孩子的乐园,那对于母亲来说,它是生活的主战场。
每天清晨,天蒙蒙亮,井台边就响起了水桶碰撞的声音。那是阿妈在洗衣、洗菜。文昌女人的勤劳,大抵都融化在了这一桶桶提上来的井水里。
那时候的水,并不总是完美的。有时候遇上旱季,或者刚下过暴雨,压上来的水会泛着微微的浑浊,甚至带着一丝铁锈味。阿妈总是不慌不忙,把水打在缸里,静置半晌。
等到傍晚,水缸里的水便清澈见底。阿妈用这水煮出的番薯粥,在这个海滨小城潮湿的空气里,氤氲出最安心的烟火气。
04 别了,老屋的守望者
后来,时代变了。
村村通了自来水,一拧龙头,水就来了,既不用“引水”,也不用费力气压。那个曾经被视为家庭重器的压水井,慢慢成了院子里的配角。
一开始,老人还舍不得,总觉得自来水有股“漂白粉味”,坚持要用井水浇花、洗地。再后来,年轻人去了城里,老屋空了,压水井也彻底闲了下来。
回文昌老家扫墓,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,院子里的杂草已经没过了脚踝。那口压水井还立在墙角,只是铁柄已经锈死,再也压不动了。出水口上结了蛛网,井台上长满了青苔。
它就像一位完成了使命的老兵,静静地站岗,看着时光在红砖墙上剥落,看着头顶的椰子树落了又长。
我试着找来一瓢水,想再试一次“引水”,水倒进去,却瞬间消失在干涸的泵体里,听不到一点回响。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有些时光,就像这倒进去的水,再也引不回来了。
但在某个午后,或者在异乡拧开水龙头的瞬间,我依然会怀念那一声“咯吱——”。
那不是噪音,那是故乡的心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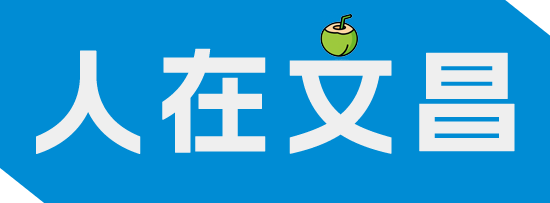 人在文昌
人在文昌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