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个讲究速度的时代,我们似乎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抵达对岸。
直到有一天,跨海大桥的霓虹亮起,那个满身柴油味、叼着卷烟的摆渡人,默默解开了缆绳,最后一次熄灭了引擎。
01
“再不走,就来不及了。”
文昌清澜港,海风里夹杂着咸腥和机油的味道。
老陈(化名)眯着眼,看了一眼头顶那座横跨天际的庞然大物——清澜大桥。那是2012年,桥刚通车不久。
在桥下,他的木头渡船像一片飘摇的树叶。

木头渡船
过去的三十年里,他是连接清澜镇和东郊椰林的“腿”。那时候没有桥,想去对面那片浩瀚的椰子林,或是从东郊把刚摘的椰子运出来,全靠老陈他们这帮摆渡人。
那时的渡口,是文昌最喧闹的地方。
早晨五点,渡口就醒了。摩托车的轰鸣、挑担菜农的吆喝、学生们的嬉笑,还有那句地道的文昌话:“阿叔,今日浪大不大?”
老陈总是笑笑,不说话,手里稳稳地把着舵。
船舱里总是挤满了人。人挨人,鸡鸭鹅在笼里叫。大家在船上抽烟、聊家常,短短十几分钟的航程,是一个微缩的社会。
那时候日子很慢,慢到需要在渡口排队等上好一会;慢到遇上台风天,整个东郊镇就像一座孤岛,只能隔海相望。
那时候,摆渡人是英雄。因为没有他们,海就是无法跨越的墙。
02
可是,时代不会因为谁的留恋而停下脚步。
变化是从打桩机的声音盖过海浪声开始的。
老陈看着那一根根巨大的水泥柱子插进海底,看着钢筋水泥在头顶慢慢合拢。那是清澜大桥。后来,更远的地方又有了连接海口与铺前的海文大桥。
“天堑变通途”,新闻里都这么说。
对文昌人来说,这是天大的好事。以前从铺前到海口,坐渡船要看老天爷脸色,稍有风浪就停航,绕路要走几十公里山路。现在,海文大桥一通,二十分钟,天涯变咫尺。
急救车能过去了,台风天也能回家了,游客们的车队像长龙一样开进了铺前古镇。
效率战胜了等待,钢铁战胜了木船。
但对摆渡人来说,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。
随着大桥通车,渡口的人流肉眼可见地少了,慢慢消逝在时光里。
曾经热闹得像集市一样的码头,突然变得空旷而寂寥。
03
那是最后一班船。
我记得那天,夕阳把海面染成了血红色。
老陈像往常一样,把船靠岸,搭好跳板。没有蜂拥而上的人群,只有两个背着书包的学生,推着自行车上了船。
“阿叔,听说以后不开了?”学生问。
老陈磕了磕烟斗里的灰,低声说:“嗯,桥通了,大家都方便了,我也该歇歇了。”
船开得很慢,似乎是故意的。老陈的手抚摸着那个被磨得发亮的舵柄,那是他三十年的老伙计。这艘船,送过难产的孕妇去医院,送过考上大学的孩子去省城,也运过数不清的文昌鸡和椰子。
海浪拍打着船身,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,像是在低声呜咽。
头顶上,清澜大桥上车流如织,车灯连成一条流动的光带,呼啸而过。脚底下,老旧的柴油机发出沉重的喘息。
这一刻,上方是呼啸而过的现代文明,下方是默默退场的旧日时光。
船靠岸了。老陈看着那两个学生骑车远去,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掉头,而是站在船头,点了一支烟,久久地望着对岸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。
那一夜,他熄灭了引擎,也熄灭了一个时代。
04
有人问,大桥通了,我们失去了什么?
我们其实什么都没失去,我们得到了速度,得到了安全,得到了繁荣。
只是,我们再也找不回那种“等待”的心情了。
我们再也闻不到混合着海风和柴油的味道,再也听不到渡船靠岸时那声沉闷的碰撞声,再也看不到那个在风浪中为你守候的身影。
后来的后来,我去过海文大桥下的铺前港。那里曾经也是海南最险要、最繁忙的渡口之一。如今,那座被称为“抗震抗风”的宏伟大桥横跨海面,壮观得令人屏息。
而在大桥的阴影里,废弃的渡口长满了青苔,几艘破旧的木船搁浅在沙滩上,任由风吹雨打。
这就是现实。所有的便捷,背后都有人默默退场。
05
致敬那些文昌老渡口的摆渡人。
他们是水上的游牧民族,用半生的时光,缝合了两岸的距离。在大桥未起之时,是他们用血肉之躯,摆渡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。
在清澜大桥或海文大桥下那片波光粼粼的海面,那里曾有一艘船,摆渡过岁月,也摆渡过人心。
桥是通往未来的路,而渡口,是我们回不去的故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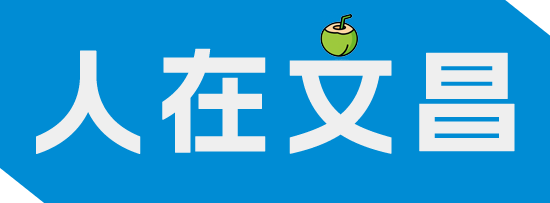 人在文昌
人在文昌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