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上学,现在的孩子记忆可能是“铃铃铃”的电子乐,或者是标准的广播声。
但对于在那片椰林下长大的文昌孩子来说,上课和下课,只有一种声音: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
那是一块悬挂在老榕树或者屋檐下的铁皮铃铛。
它可能是一个报废的卡车轮毂,也可能是一块不知从哪拆下来的厚铁板。它浑身锈迹斑斑,被一根同样生锈的粗铁丝系着,吊在半空。

它虽然丑陋,虽然粗糙,但当那个看校门的阿公拿起铁棍,重重地敲下去时,那个声音,足以穿透最嘈杂的蝉鸣,穿透文昌午后最粘稠的湿热,直抵人心。
那个掌握时间的“阿公”
在文昌的乡镇小学,总有这样一个看校门的阿伯,或者阿公。
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汗衫,脚上一双旧拖鞋,手里常年夹着一支烟,或者拿着长长的烟斗。他不用看表,仿佛身体里就有一个生物钟。
每当太阳爬上椰子树梢,或者影子缩到脚底下时,他就会慢悠悠地走到那棵大树下。
手里那根磨得光亮的铁棍,就是他的指挥棒。
“当!当!当!当!”
声音急促而有力。
这是上课铃。这声音像一道命令,原本在操场上疯跑、在沙地里打弹珠、在树下丢沙包的孩子们,瞬间像受惊的鸟群,呼啦啦地往教室里钻。
拖鞋拍打地面的声音,混合着铁皮的震动,那是童年最慌张也最生动的节奏。
而到了下课铃,阿公的敲法又不一样了。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
节奏舒缓了一些,余音拉得很长。
这时候,那块铁皮发出的简直是天籁之音。老师的粉笔字还没写完,我们的心早已飞到了校门口的小卖部。
铁皮下的文昌味道
那块铁皮铃铛,挂在文昌的红砖瓦房下,见证了太多专属那个年代的画面。
记得那时候的教室,多半是老式的南洋风格建筑,或者是祠堂改建的。窗户是木制的,没有玻璃,风一吹,椰子叶的沙沙声就伴着读书声一起进来。
那是真正的“风声雨声读书声”。
那时候的我们,甚至没有统一的校服。大家穿着短裤短衣,皮肤晒得黑亮,像文昌海边顽强的石头。
夏天很热,头顶只有那种老式的吊扇,转起来“嘎吱嘎吱”响,仿佛随时会掉下来。我们一边用课本扇风,一边盯着窗外那块铁皮。
那时候没有空调,但有树荫;没有手机,但有伙伴。那时候的快乐,就像那块铁皮发出的声音一样,简单,直接,清脆,没有任何杂质。
消失的回响
后来,我们长大了。我们离开了文昌,去了海口,去了北上广,去了更远的地方。
我们听过无数种铃声。机场的催促广播,写字楼的电梯提示音,微信的视频邀请声。
精致,悦耳,但没有温度。
回头看,曾经的小学可能已经不在,曾经的铁皮铃铛也不见了。
那一刻,心里空落落的。
我们怀念那块铁皮铃铛,其实不仅仅是怀念一个旧物件。我们怀念的,是那个听到铃声就拼命奔跑的自己;是那个一放学就有人喊你名字的黄昏;是那个空气里飘着抱罗粉香味、日子慢得像牛车一样的旧时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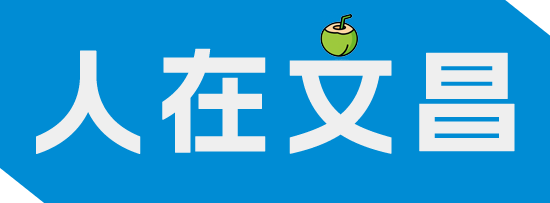 人在文昌
人在文昌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