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海南文昌,流传着一句老话:文昌深厚的文化底蕴,是一代代读书人用心铺就的。
而在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中,有一个人,如同一座孤高的山峰。
他与丘濬(jùn)、海瑞并称为“海南三贤”。但相比海瑞的刚烈、丘濬的博学,他的故事里,藏着更多关于“选择”和“归宿”的温情。
他叫邢宥。
一个曾在大明王朝权力中心游刃有余,却在最辉煌时,选择转身回家的人。

宦海浮沉,唯一的行囊是傲骨
公元1416年,邢宥出生在文昌的一个书香世家。
那时的海南,仍是中原人眼中的“天涯海角”,荒蛮偏远。对于这里的少年来说,想要跨越琼州海峡,走到权力的中心北京,难如登天。
但邢宥不仅走出去了,还走得很漂亮。
22岁中举,32岁考中进士。那个从椰林海浪中走出的青年,终于站在了紫禁城的金銮殿前。
史书记载他:“博极群书,不仅有才,更有识。”
他初入仕途,便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。这是一个什么官?专司风纪,纠劾百司,上管皇亲国戚,下察贪官污吏。
在那个官场染缸里,邢宥活得像个异类。他巡按四川、福建、浙江,所到之处,贪官闻风丧胆。
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苏州。当时的江南,富甲天下,也积弊深重。邢宥被委以重任,巡抚江南,不仅治水安民,更锐意革新。他大刀阔斧清理积案,将那些盘根错节的豪强势力一一整肃。
百姓爱戴他,称他为“邢青天”。
朝廷倚重他,那时他已官至右佥都御史,出巡地方,实为封疆大吏,手握重权。
如果剧本这样写下去,他会是一代能臣,位极人臣。
但邢宥,偏偏不按剧本活。
官游苏杭,两袖清风
在苏州、杭州这等天下最富庶之地为官,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“美差”。
多少官员在此迷失,但邢宥任职数年,留下的记录却让后人肃然起敬。
史书仅用四字概括,却重如千钧:“囊橐萧然。”
意思是,他的口袋和行囊,空空如也。
他在最繁华的人间天堂,掌管着最重要的钱粮民生,自己却过着清简如水的日子。离任之时,百姓夹道相送,有人欲赠金银,他严词拒绝;有人奉上土仪,他也婉言谢绝。
他带走的,只有几箱沉重的书籍,和两袖浩荡的清风。
他曾写诗自白:
“平生不蓄黄金产,这片冰心只自知。”
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,保持欲望的清醒,远比获得权力更为艰难。邢宥做到了。
高处不胜寒,不如归去
邢宥的一生,有一位至交好友,便是后来官拜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。
当时朝中流传着“丘文庄之头,邢襄惠之项”的说法,将两人比作支撑朝堂的头脑与脊梁,足见其地位与情谊。
二人常在京城对酌,纵论天下。丘濬深知其才,极力挽留他在朝中辅佐社稷,认为他有宰相之能。
然而,在成化年间,五十余岁的邢宥,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:
辞官,归乡。
非因党争失利,亦非身体衰颓。
理由纯粹而坚定:回乡奉母,尽人子之孝。
他的母亲年事已高,独在海南故里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这句古训,于邢宥而言,是刻在心头的警醒,而非口头虚言。
皇帝再三挽留,同僚多番劝阻。
邢宥去意已决,上书陈情,辞恳意切。
“官可以不做,母亲不能不养。”
公元1470年左右,时年五十四岁的邢宥,终于卸下那一身象征权力与荣耀的官袍,换上布衣,登上了南归的海船。
彼时,丘濬在京城扼腕叹息,痛失臂助。
而邢宥,立于船头,望着越来越清晰的文昌海岸线与椰影,内心想必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平静与充盈。
回乡十余载,只留书香满乾坤
回到文昌的邢宥,并未凭借余威成为地方乡绅,也未购置良田华宅。
他在文昌水吼村的祖居旁,筑起数间茅屋,取名 “湄丘草亭”,自号“湄丘道人”。
昔日令贪官胆寒的“邢都堂”,变作一个箬笠草鞋、于乡间悠然漫步的寻常老者。
他谢绝地方官员的拜谒,也不干涉地方政务。
唯倾心于一事:读书,著述,教诲后生。
他深谙,海南被视为蛮荒,根源在于教化未兴。晚年他潜心整理海南地方文献,孜孜不倦地提携奖掖家乡学子。他将自己的藏书开放,供年轻士子阅读研学。
他与千里之外的丘濬,依旧书信不绝。丘濬在朝中主持修史编书,常驰书向这位隐居的挚友请教切磋。
邢宥在家乡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,直至六十五岁逝世。
这十年,于大明庙堂而言,少了一位股肱之臣;
但对于文昌,对于海南而言,却多了一位文化的播火者与守望者。
他去世时,家徒四壁,唯余满室书香,千古文章。
写在最后
在邢宥身上,我们看到的远不止“清廉”二字。
更是一种知进退、明取舍、重根本的人生大智慧。
年轻时,他有 “兼济天下”的雄心,故而义无反顾,北渡求学求仕;
为官时,他有 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定力,故而清风两袖,屹立于繁华之地;
巅峰时,他有 “弃官寻亲”的深情,故而拂衣而去,甘归于椰风海韵。
今天的文昌,文脉绵延,人才辈出。
走在文昌的路上,或许依然能在风中感受到那种穿越了六百年的精神回响——
无论走多远,飞多高,都要记得那颗赤子之心,和那条回家的路。
参考资料:《明史》、《琼台志》、《文昌县志》、邢宥《湄丘集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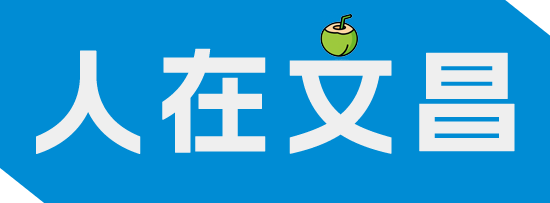 人在文昌
人在文昌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