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拔牙,文昌阿婆嘴里总有一套比牙医更严谨的“学术理论”。
小时候,牙齿一开始松动,就是一场漫长的心理战。舌头总是不由自主地去顶那颗摇摇欲坠的乳牙,吃饭时小心翼翼,生怕咬到硬物。那种酸软又带着一丝痛痒的感觉,像极了那个年纪无处安放的躁动。
等到牙齿终于摇摇欲坠,只剩一点皮肉连着时,家里的“牙科手术”就开始了。
第一步:骗局与棉线
如果是阿公动手,他通常会找一根缝衣服的白棉线。手法相当传统:一头拴在摇晃的牙齿上,另一头攥在手里。
“来,张嘴,让我看看松到什么程度了。”阿公一脸慈祥,仿佛真的只是为了检查。
你刚张大嘴,还没来得及从嗓子眼里发出“啊”的一声,阿公的手就像练过功夫一样,猛地一拽。
没有任何麻药,只有那一瞬间的惊愕和随之而来的咸腥味。牙齿已经挂在棉线那头荡秋千了。
第二步:双脚站齐的“神圣时刻”
拔下来不是结束,而是仪式的开始。这才是文昌孩子最紧张的环节,因为这关乎未来——也就是所谓的“颜值”。
阿婆会让你拿着那颗带着血丝的小牙齿,走到老屋的屋檐下。如果是下排的牙齿,必须扔到屋顶上(寓意向下长的牙要往上长);如果是上排的牙齿,则要丢到床底下或者土坑里(寓意向上长的牙要往下长)。

若是丢屋顶,规矩最大。
“站好!脚跟并拢!脚尖对齐!”阿婆在旁边像个严厉的教官。
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,只知道必须要像立正一样,双脚死死地并在一条线上,站得笔直。
阿婆说:“脚站得齐,以后长出来的牙齿才会整齐。要是脚站歪了,以后牙齿就长得东倒西歪,像那个被风吹乱的甘蔗林。”
这句恐吓对于一个爱美的小孩来说,威力巨大。于是,我屏住呼吸,脚后跟紧贴脚后跟,手里紧紧捏着那颗小牙齿,眼睛死死盯着瓦房顶上某一片瓦。
第三步:完美抛物线
“扔!”一声令下。
我用尽全身力气,把手里的牙齿向上一抛。
那颗牙齿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。如果运气好,你会听到清脆的一声“叮——”,那是骨质的牙齿撞击陶土瓦片的声音。牙齿随后会顺着瓦槽滚落,或者卡在两片瓦之间,永远地成为了老屋的一部分。
有时候扔完还得念两句童谣咒语,比如喊着把旧牙给老鼠,换回一颗新牙(“老鼠牙,换新牙”),因为老鼠的牙齿最硬、长得最快。
写在最后
做完这套动作,才算真正松了一口气。赶紧跑去水缸边漱口,还要时不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没有站歪,生怕刚才那一下没站稳,毁了未来一口好牙。
如今,看到那些布满岁月痕迹的瓦房顶,我偶尔会想,那上面层层叠叠的瓦片缝隙里,是不是还藏着我那几颗没长齐的乳牙?又或者,当年那一声清脆的“叮”,其实就是我们在年代里,对成长许下的最庄重的愿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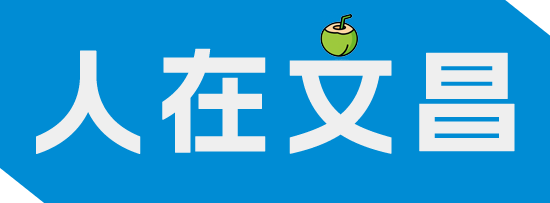 人在文昌
人在文昌









